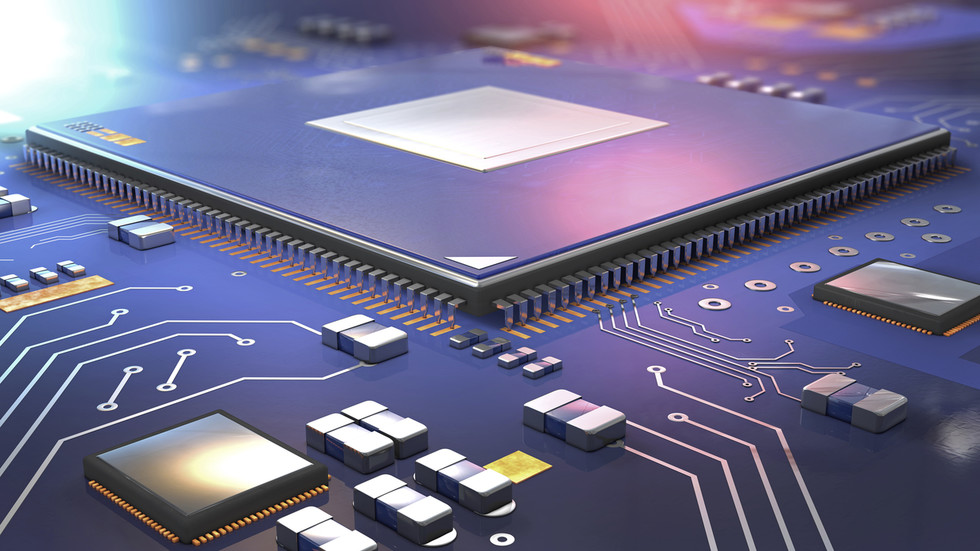守株待兔出自(大梦春秋021|揠苗助长、守株待兔——人们为何喜欢嘲笑宋国人?)
从某种角度说,出生在春秋时期的宋国,是一件令人郁闷的事。
是的,宋国是商朝之后,于周为客,可以不纳贡,可以行老礼儿,遵奉当年商朝的礼仪。但宋国毕竟是“亡国之遗”,是失败者的后裔,周朝不绝其祀,优待有加地把它供起来,又是立国,又是封公,一方面是遵循“兴灭国,继绝世”的古礼,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显示周室的慷慨仁慈,宽容大度。
这种保护性的优待里面,即便有尊重的成分,也十分稀薄。
胜者为王,高高在上,失败者只能接受弱者的地位,被胜者安排,被胜者驱使,或者被胜者嘲笑,这是亘古不变的铁律。
至迟从春秋后期开始,嘲笑宋人,拿宋人开涮就成了一种风尚,各种关于宋人的段子层出不穷。这些段子,少数堂而皇之出现在《左传》《战国策》这样的史书里,多数被搜罗进《韩非子》《吕氏春秋》《孟子》《庄子》《晏子春秋》《列子》等诸子书中。虽然这些古书并非专门嘲笑宋人,它们时常也讲讲齐人、郑人、杞人(杞乃夏朝的“亡国之遗”,命运与宋国十分相似,关于杞国的一个著名段子是“杞人忧天”)的笑话,但和宋人比起来,则是小巫见大巫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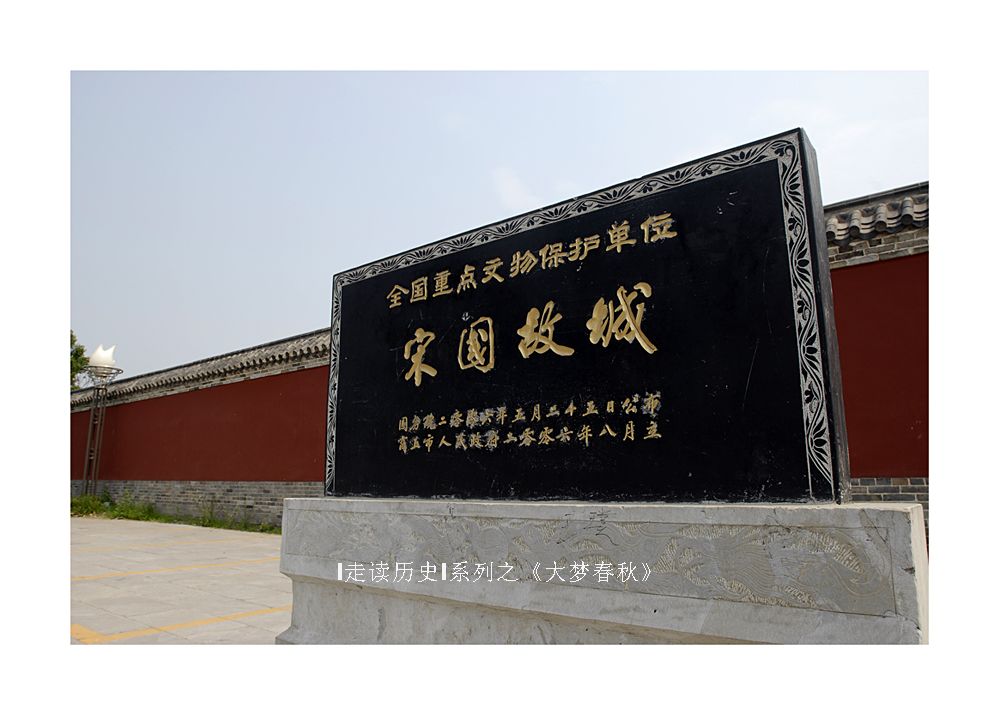
河南商丘,宋国故城
在中国有两个知名度极高的成语,“揠苗助长”和“守株待兔”,堪称段子中的极品。
“揠苗助长”出自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:
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,茫茫然归,谓其人曰:“今日病矣,予助苗长矣。”其子趋而往视之,苗则槁矣。
“守株待兔”出自《韩非子·五蠹》:
宋人有耕者。田中有株,兔走触株,折颈而死。因释其耒而守株,冀复得兔。兔不可复得,而身为宋国笑。今欲以先王之政,治当世之民,皆守株之类也。
在这两则经过高度提炼的段子中,主人公都是宋国的农民。如果说“守株待兔”这样的事多少有可能发生的话,那么“揠苗助长”无论如何令人难以置信,因为农民天生与土地在一起,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五谷禾稼的生长有如太阳东升西落一般,早已成为他们生命中最基本的常识,绝无可能出现“予助苗长矣”这类蠢事,除非他缺心眼儿,是个傻子,这涉及到智商问题。
实际上,诸书嘲笑宋人时,出发点多数与智商无关,他们嘲笑的是宋人的迂腐、不知变通、幼稚、鲁莽等所谓的人生智慧,“守株待兔”是其典型代表,与此类似的则不胜枚举。
比如,《战国策·魏策》中说,有一个宋人,外出求学三年,回家后整个人都变了,见了老母亲竟然直呼其名。他妈很诧异:你学习了三年,怎么越学越糊涂,连妈也不喊了?此人振振有辞地回答:世间贤人莫过于尧、舜,万物之大无过于天、地,尧、舜、天、地,我不都是直呼其名吗?母亲你贤不如尧、舜,大不过天、地,我当然要喊你名字了。他妈长叹一声:学来的东西,难道你要全部照搬不误?就算要照搬,妈还是要喊的吧!
在《吕氏春秋·淫辞》中,这种迂腐和不可理喻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:有个名叫澄子的宋国人丢了件黑色衣服,他就跑到街上去找。找着找着,忽然看见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走来,他上前一把抓住那女人,要脱掉她的衣服。女人说:你干嘛?他说:我丢了件黑衣服。女人说:你丢黑衣服关我什么事?我这件衣服是我自己做的。丢衣服的人不耐烦了:哎呀,赶紧把这衣服给我吧,昨天我丢的黑衣服是纺丝的,你这件不过是单面的,用单面的抵偿纺丝的,你可是占了大便宜啊!
故事到此戛然而止,不知道那女人是否抽了澄子一个嘴巴。
诸书之中,最喜欢嘲笑宋人的是《列子》。
在《列子·杨朱》中,一个穷困潦倒的宋人,连过冬的衣服都没有,却在晒太阳时感受到了莫大的舒适,以为人生最大的幸福不过如此。他对自己的老婆说,如果把晒太阳所得之享受献给国君,或许能得到重赏。
而在《列子·说符》中,一个在街上闲逛的宋人捡到了一张借条,他喜不自禁地拿回家里,翻来覆去地看,最后实在忍不住了,跑去告诉邻居:我要发财了!
显然,这张借条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财富,就像那位晒太阳的宋人无法从国君那里得到任何奖赏一样——事实上,他连见到国君的可能性都没有。《列子》借此嘲讽宋人的无知和愚蠢,其辛辣程度丝毫不亚于“揠苗助长”“守株待兔”之类。
那么,东周列国的知识分子们为何要嘲笑宋人呢?

商丘,阏伯台
正像前面所说,宋国是弱者,遭受强者们的嘲笑是它的宿命,这是原因之一。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文化、习俗上的差异。宋国虽然是周室的封国,但因有“为客”的特权,得以保留商代的许多文化、礼仪、习俗。这特权本身就让其他诸侯眼红,所以,但凡宋人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,都成了其他国家挖苦、嘲讽宋国的理由。他们把宋国视为异类,想尽办法编排宋人——有可供嘲笑者,则大肆嘲笑,没有可供嘲笑者,就创造条件去嘲笑,最后势必出现如下情况:把发生在别国的蠢人蠢事也挪借到宋人头上。
段子就是这样产生的。
被视为异类的宋国,只能无可奈何地成为其他诸侯批发段子的集散地。
公元前7世纪中期,宋襄公子滋甫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被嘲笑、被视为异类的国度,而他的人生也因此成为被嘲笑的对象,成为一连串段子的诡异组合。
关于子滋甫的第一个段子,出现在公元前652年。
这一年冬天,在位三十年的宋桓公子御说被一场疾病击倒,他清晰地感觉到了死亡的日益临近。当子御说准备把国君之位传给太子子滋甫时,子滋甫竟然推辞不受,他说:目夷年长,而且素有仁爱之名,不如把君位传给他吧!
此事非同小可,子御说自然十分惊讶,但子滋甫言辞恳切,再三请求,子御说只好把公子目夷找来,说要把君位传给他。
目夷字子鱼,是子滋甫同父异母的哥哥,他闻听此言,连忙拒绝:能以国相让,还有比这更能称为“仁”的么?仅此一点,我就自叹弗如;况且,舍嫡而立庶,不合国家的礼制和习俗,我不能接受!说完,子鱼逃也似的退了出去。
事情至此,已经别无选择,宋国国君之位非子滋甫莫属,任他再如何推辞,子御说都不可能再改变主意。

商丘,阏伯台
第二年,即公元前651年春天,宋桓公子御说辞世,子滋甫即位,是为宋襄公。
此年夏天,正当丧服未除之际,子滋甫忽然接到消息,齐桓公姜小白要在葵丘大会诸侯,盛情款待天子的使者宰孔。子滋甫不敢怠慢,他把国家政事交由大司马子鱼全权处理,然后收拾行装,赶赴葵丘之会。
正是这次戴孝赴会,引起了后世无数人的口诛笔伐:你不是对国君之位没那么大兴趣嘛?你不是要让贤嘛?怎么现在这样急切地跑去参加诸侯大会?为了取得霸主和诸侯的认可,连给老爹戴孝这样的大事都不放在心上,你这么着急干吗?莫非……你所谓的“让贤”仅仅是做个样子,真正的目的是捞取“仁义”的名声?
在一个为争夺权力不惜骨肉相残的时代,子滋甫让贤的举动的确令人难以置信。但是,如果子滋甫能够穿越时空和未来世界的人展开辩论,他可以轻易找到辩护理由,令质疑者哑口无言:如果让贤是表演,表演一下意思意思也就算了,为何他要“再三请求”?万一子鱼答应了,又当如何?须知,宋桓公子御说已经答应了子滋甫的请求,只要子鱼一点头,下一任宋国国君就会变成子鱼。
因此,子滋甫让贤的诚意是可信的,而且让贤也并不说明他对国君之位没有兴趣。退一步讲,就算他真的没有兴趣,可是一旦他坐上那个位子,维持国家运行的一整套机制就会发生作用,推着他向前,迫使他去履行一个国君的职责。只要他不是一个弱智或者无可救药的暴君,那么这个国家起码可以沿着既有的路线走下去,而不至于出什么大的乱子。
子滋甫从父亲手中继承的这个国家,从地理位置而言,与西邻郑国十分相似。两个国家都处在中原华夏世界和南方楚国势力范围的交界处,国都四周又都是平原,缺乏天然的军事屏障,极易遭到攻击。这样的地理位置,意味着宋国也和郑国一样,面临着一个“站队”的问题——当华夏世界和南方的楚国发生冲突时,该站在哪一方呢?
郑文公姬捷是一个典型的“骑墙派”,他没有原则,谁更加强硬,更有威胁,他就站在谁的一方,所以数十年来郑国时而追随齐国,时而投靠楚国,随齐时楚来攻,投楚时齐来伐,反反复复,少有宁日。宋桓公子御说恰恰相反,他在公元前680年由于背叛北杏之盟,遭到齐、陈、曹联军讨伐,此后便一心一意追随齐国,再未作出任何背叛齐国的事情。至于霸主姜小白发起的各种行动,宋国几乎无一例外全部参加,成了齐国最忠实的盟友。大树底下好乘凉,正是因为宋国奉行了铁心追随齐国的外交路线,子御说在位三十年,宋国局势稳定,基本没有遭到外敌的侵袭。这几乎是宋国历史上最安定的一段时间。

《左传·僖公八年》书影
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追随齐国已经成为宋国的一项基本国策,子滋甫深谙其中道理。所以在姜小白一生中最重要的葵丘之会,子滋甫必须参加,哪怕因此遭到别人的质疑和冷眼。
在此后的几年间,子滋甫严格遵循着乃父制定的这项基本国策,唯齐国马首是瞻,但凡姜小白召集的活动,从不缺席:
公元前651年秋天,参加葵丘之盟;
公元前648年,为卫国修筑楚丘;
公元前647年,与齐、陈、卫、郑、许、曹会于碱(卫地,在今河南省濮阳市东);
公元前646年春,为杞国筑缘陵;
公元前645年春,与齐、陈、卫、郑、许、曹会于牡丘(在今山东省聊城市东)……
子滋甫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,仁义的名声和对齐国亦步亦趋的追随,使他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——在姜小白去世之前的某一年,他担心自己身死之后儿子们会因争权而大打出手,因此和管仲商议,把太子姜昭托付给了宋襄公子滋甫。
子滋甫从这件事中,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,此前,他或许连想都没有想过。
甚至可以说,姜小白此举成了子滋甫国君生涯的转折点。
一股强烈的激情裹挟着子滋甫,令他欲罢不能。
(待续。文图俱为原创,盗用必究)
///^_^